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肖潇 北京报道
近日,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开炮“低价战”,指责相关互联网平台“让价格体系下来,对中国品牌、对中国的产业是一种巨大的伤害”。钟睒睒的批评,再次将商家对电商平台过度低价的强烈不满推向公众视野,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思考契机。
回看2023年,或许是电商行业价格竞争最激烈的一年。这一年,率先用低价击穿市场的拼多多,靠Temu在海外继续高歌猛进;京东推出了百亿补贴频道,重启京喜和京东拼拼;淘宝天猫集团将“价格力”列为五大战略之一,首次在双11期间实施天天低价策略;抖音电商启动了“0元入驻”活动,吸引了大量中小商家的加入;快手则明确提出了“低价好物”战略,并上线了“大牌大补”的核心玩法。
研究电商数十年、执笔商务部《电子商务报告》,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欧阳日辉注意到一些新现象。他发现从去年开始,电商平台一边在卷低价,似乎让消费者充分享受到了低价“福利”;但与此同时,消费者“一边买一边骂”,特别是某些平台的产品质量暴雷屡屡发生,商家和工厂苦不堪言。
在欧阳日辉看来,过度低价竞争的问题已经现形,一些电商平台的流量不成比例地流向低价,商家不惜偷工减料或抄袭造假,陷入“囚徒困境”。在市场发展过程中有价格竞争很正常,但如果超出了合理范围,就会伤及所有市场参与者。
如今低价竞争究竟到了什么程度?为什么难以监管?该如何打破这一困局?在中国市场学会近日举办的“构建良好电商生态 推动电商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上,多位业内学者、商家从价格竞争的视角讨论了这一系列问题。
商务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研究院院长李鸣涛认为,造成当前局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只要一家平台率先推出一个有利于低价攻占市场的规则——超大额满减、自动跟价、仅退款、强制运费险……其他平台就只能被动跟进,低价竞争进入没有底线的恶性循环。李鸣涛建议,治理应该以平台规则为抓手,压实平台责任。
“伪低价”陷阱
过度低价竞争的局面里,“以次充好”是商户们会主动提及的问题。
江苏淮安商家刘晓平组织了当地的商家互助会,他了解到一个羽绒服厂家的经历:原本厂家定价189元的儿童鹅绒羽绒服,在P平台上被强行降价到99元后,厂家不得不选择用pp塑料颗粒填充,制造出高蓬松度的假象。除非拿到专业的检测机构检测,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出面料成分的真假。
让刘晓平更担忧的是,消费认知会渐渐被这样泛滥的“次品”改变。“再拿内裤来说,平台现在很流行29.9元七条内裤,声称100%纯棉、低价来自该平台补贴,但事实上它的棉含量可能不到1%。长此以往,消费者可能认为七条纯棉内裤的价格就应该是29.9元,市场想再生产真正的纯棉内裤,就会因为价格太高,没人想要了。”刘晓平无奈地说。
另一位商家冯真源也说,“劣质驱逐良币”的情况已经冲击到了商家生存,尤其是具备工厂生产能力的厂家。
冯真源所在的广东阳江市是厨房刀剪的主要生产地,他提到,最初他从淘宝开始做起,尽管当时也有低价商品,但它们和高价产品各有定位、不必直接竞争。如今一些平台会对“更低价”设置明确门槛,流量分发也采用绝对低价战略,“谁便宜就推荐谁”,假冒伪劣产品便有了制作动力——现在许多热销假货的售价,甚至比阳江正品成本还低50%。
冯真源用“伪低价”形容这种局面。一方面,低价商品以次充好、质量无法保证;另一方面,正品商家为了控制亏损,也只能迎合平台的低价逻辑,进行低价甩卖。冯真源粗略估算,自去年开始,当地有超过三成的工厂因此陷入运营危机。
对于中小商家来说,这是一个被迫卷入的两难困境。中国市场学会会长夏杰长解释,商家如果降价,就能得到平台的算法推荐和流量倾斜,可这意味着得压缩利润、牺牲产品质量;但如果商家不降价,他们需要去投广告和直播间来“引流”,承担高昂的营销费用,经营成本又会进一步抬高。
困境背后:消费者和平台的双重选择
电商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过度低价竞争局面的?
消费降级,是参会人员首先提到的因素。艾瑞咨询披露的《2023年中国电商市场研究报告》显示,2023年,国内网购用户选择网站/APP看重的诸多因素中,“价格-价格优惠度”排名第一,低价在主导越来越多的消费决策。
消费者的需求,倒逼了电商降低产品价格,但这不同于传统的市场低价竞争。夏杰长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电商平台是典型的双边市场,平台需要设定双边的“收费要求”。
通俗点说,就是平台会对商家、消费者设定不同的价格水平,而一般平台都对消费者的“收费要求”更宽容,因为消费者可以带来流量等其他好处。所以,当消费者普遍追求低价,平台便把低价作为核心指标作用到商家身上。
参会商家都提到了对一些平台的超大额满减规则、自动跟价系统、流量绝对倾斜低价的不满。夏杰长认为,目前我国电商低价竞争的现象,本质还是电商平台的算法和流量规则带来的。
平台之所以会纷纷设计此类规则,原因之一是流量增量几乎见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所长杜国臣用了两组宏观数据说明:一组是全国目前的网购用户占比87%,互联网用户数达到77%,电商消费者数量难有拓展空间;另一组是社会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也已经压缩到了14.4%,加强消费体验的空间也比较有限。
“在这种存量状态下,竞争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怎么竞争?在一家先开始‘卷’价格的情况下,大家都选择了逐底的价格竞争。”杜国臣说。
选择低价竞争还离不开平台的特殊属性,尤其是平台的注意力经济逻辑。清华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认为,存量时代下,平台的获客成本水涨船高,价格战成了获得更多注意力的捷径。而“注意力又是没有办法储存的资源,平台必须要出清,要进一步把流量转化为销量。” 低价竞争的循环就此形成。
“从最原始的出发点来看,低价从来就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平台的真正目的是如何吸引更多流量并把流量变现。”夏杰长说,在低价、流量、销量组成的复杂系统中,“唯低价”“博流量”并非商家的长期生存法则,连锁引发一系列负面效果。
为什么难以监管?
疯狂价格战、假冒伪劣泛滥、行业生态被破坏……听起来不是新问题,但为什么难被监管到位?一个原因是“低价竞争”的尺度不好把握。
重庆工商大学原校长杨继瑞尤其提醒,在关注低价竞争时,要注意三个“不等于”:低价商品不等于劣质商品;商品价格降低不等于消费降级,在手机、汽车等行业的生产力发展时,就存在价格降低和消费升级并存的情况;低价竞争也不等于过度低价竞争,正常的价格竞争是市场活力的体现。
目前要治理的,是过度低价竞争。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只有一家获利、其他人都亏损;要么所有人都在亏损,“没有人是赢家,只有价格水平和盈利能力下降了。”
李鸣涛还指出,治理规定往往跟不上平台规则的更新迭代速度,而电商行业的执法成本又太高,事后能打击的数量有限,这都是监管存在的现实问题。
现场有商家提到,他们曾直接就平台规则的不合理问题进行集体起诉,但一审二审都遭败诉。究其原因,是法院认为平台规则在形式上没有违反法律法规。但在商家们看来,“其实很多规定,可能制定本身没有违法,但平台在执行上出现了问题。而法院很少考虑这一点。”
目前已经有一些监管措施出炉。比如,今年5月,国家《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发布,明确规定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服务协议、交易规则等手段,对平台内经营者的交易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该规定于9月1日落地。
此外,平台开始自行调整低价竞争的战略,今年,淘天集团在618后弱化了绝对低价战略,搜索权不再以“五星价格力”为准,更侧重按GMV(交易金额)分配;双十一附近,多个平台松绑了仅退款规则,为商家提供长期的申诉复议入口。不过现场商家坦言,他们还没感受到明显变化。
在杜国臣看来,电商的快速发展和社会要求之间,始终存在一种治理赤字,必须要承认这一客观事实,并阶段性地处理核心矛盾。治理还有不少路需要走。
如何压实平台主体责任?
李鸣涛认为,治理需要以平台规则为抓手,在此基础上调整低价逻辑,不能放任平台靠流量规则“压上游商家”。
至于到底如何压实平台责任、压实平台哪些责任,参会人员抛出了几点问题:平台更新规则前,是否需要先跟市场主体商议和公示,保障商家具有自由选择权?在涉及调整价格决策时,行业协会或市场监督机构,是否需要对规则作出评估?
参会人员都提醒,不能贸然用简单粗暴的行政化手段来监管,而要以市场、法制手段治理。可以鼓励平台完善ESG报告,或者通过行业调研、约谈警告的方式,进行柔性执法。
电商生态里,电商平台、商家、消费者、物流企业、支付机构、监管部门……多个复杂主体在相互碰撞,有效的行业监管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协调机制。
杨继瑞因此提到,有五个方面的举措缺一不可:首先,严格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价格法》,平台和商家要积极开展反低价倾销的调查;第二,明确电商平台和商家的权利义务,规范市场竞争行为;第三,精准电商行业的准入门槛,严格审核商家的资质、信誉,商品分类分级等;第四,加强对商品质量、售后服务等方面的监管,促进平台和商家提高服务质量;最后,引导行业自律。通过行业协会等组织,实施“过度低价竞争”约谈制度、警示制度、平台退出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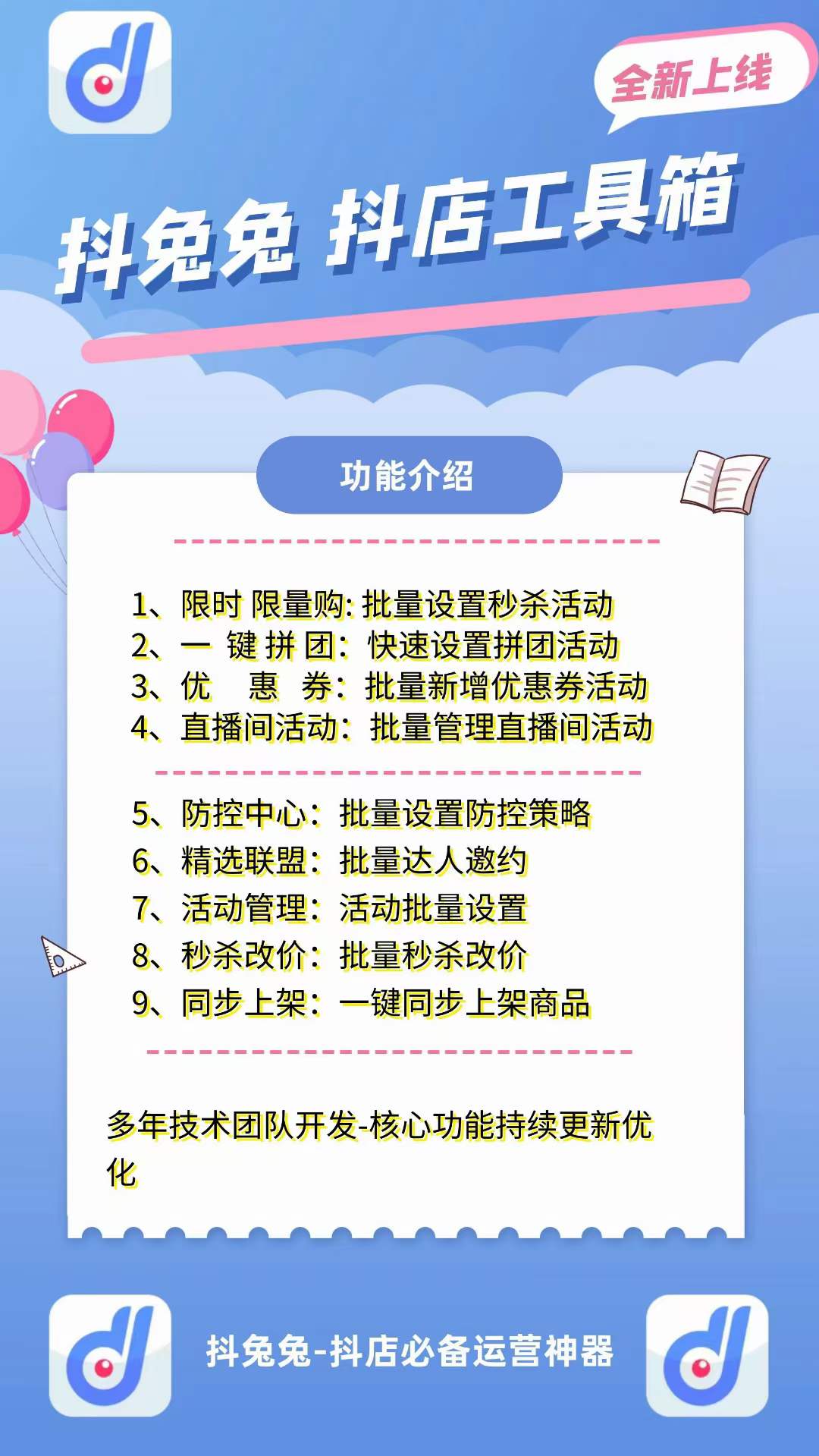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