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子商务法》的开年实施,对电商的监管管辖,也“提上议事日程”了。魏均新对此进行了探索,为大家提供一些参考和指引。
作者魏均新,系原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一位“最接地气”的干部,长期从事工商行政管理(市场监督管理)工作,其中从事法制工作20余年,是2016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系统十大法治人物,浙江省市场监管系统资深法制工作者和“业务能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已于2019年1月1日实施,作为主要实施该法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何加强各地合作,切实做好电子商务经营者(以下称“电商”)监管工作,是一个不容忽视,不容小觑的事。
2018年12月2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第2号令《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以下称“市管总局2号令”),该规章第九条和第十条对“电商”违法案件的管辖作了规定,但仅凭此并不能解决对“电商”监管管辖的所有问题,而且还可能变得更为复杂。
虽然此规定将在三个月后的2019年4月1日生效,可笔者“多事”,美其名曰“末雨绸缪”,先来个探讨,如有不当,敬请批评,欢迎反驳,当然也可以拍砖和不屑。
一、对电商平台的监管管辖
笔者认为,监管管辖与案件管辖具有一致性,也即行政机关没有监管权自然无行政处罚权,只有依法具有监管权,才有案件管辖权和行政处罚权。行政处罚权是最典型的监管权体现,因而没有行政处罚权自然也不存在监管权。
原工商总局令第60号《网络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称“原工商总局60号令”)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违法行为由发生违法行为的经营者住所所在地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辖。”市管总局2号令第九条第一款也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违法行为由其住所地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辖。”
这就表明,无论按照原工商总局60号令(2019年4月1日前),还是按照市管总局2号令(2019年4月1日起),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以下称“电商平台”)的监管,其住所所在地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都具有管辖权,包括对电商平台违法行为的查处,给予其必要的行政处罚。但由此也不能理解为,只有电商平台住所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才有监管权,特定情形下异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有监管权,包括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由于网络交易行为具有无法区分地域的特点,如果按照“违法行为发生地”的管辖规定,那么电商平台的违法行为,理论上全国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均对其有管辖权,这也是原工商总局60号令或者市管总局2号令为什么要对电商平台等管辖作特别规定的原因。也因为此,对电商平台的监管权并不完全“集中”在其住所所在地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仍然有例外。
食药总局令第27号《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二十一条第四款规定“因网络食品交易引发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危害后果的,也可以由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发生地或者违法行为结果地的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管辖。”
假设杭州的一个消费者,通过上海的一个食品经营电商平台下单购买了该平台内南京电商销售的食品,且在杭州家中吃了该食品发生食物中毒事件,那么按照上述规定,杭州的市场监管部门对此具有管辖权。如果经调查,上海平台也存在违反食品安全法的行为,那么杭州的市场监管部门应有权对上海平台实施行政处罚。
需要说明的是,市管总局2号令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并不当然排除原食药总局27号令的上述规定。同一部门的其他规章,包括原“三总局”公布的规章,作出的在特殊情形条件下的案件管辖规定,即便存在与市管总局2号令的“差异”,也不属于规章之间规定不一致的情形,不存在同一部门规章之间规定冲突的“新法优于旧法”“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原则的适用。道理很简单,市管总局2号令未作特定情形下管辖规定,并不是排斥其他规章不可以作此规定。
二、电商“实际经营地”概念和范围
市管总局2号令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平台内经营者的违法行为由其实际经营地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辖。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住所地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先行发现违法线索或者收到投诉、举报的,也可以进行管辖。”
此规定已颠覆了自2010年7月以来,原工商总局49号令《网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六条所确定的,平台内经营者由平台经营者住所所在地监管部门管辖的监管体制(2014年1月将49号令修订为60号令,对此未作实质性变动,仍然体现在其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中,即“对于其中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开展经营活动的经营者,其违法行为由第三方交易平台经营者住所所在地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辖。…管辖异地违法行为人有困难的,可以将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情况移交违法行为人所在地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市管总局2号令虽然改变了原网络交易(电子商务)的监管体制,解决了旧体制案件大量外移、相互推诿等问题,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
第一,“也可以进行管辖”存在认识差异。有人认为电商平台住所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先行发现或者收到投诉、举报的,可以管辖,也可以不管辖,具有裁量选择权;也有认为,所谓“也可以”不是选择性用语,而是确定性用语,含义是也有管辖权。之所以不用“应当”“必须”词汇,主要是因为此管辖非电商平台住所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独有”,而是存在“共同管辖”。因而电商平台住所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在“也可以进行管辖”的状态下,没有“可以不进行管辖”的选择权,不得将发现的案件线索或者接到的投诉举报移交给其他有管辖权的市场监管部门。笔者倾向于后者。
第二,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不一致。电商擅自改变注册的经营地址,包括不在注册地经营的“失联”情形。这类状况,市场监管部门一旦无法联系,会按照规定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但按照“实际经营地”管辖原则,这类情形会导致注册地反而没有管辖权的“悖论”,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注册登记管理差距较大。
第三,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存在合法分离状况。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做好电子商务经营者登记工作的意见》(国市监注〔2018〕236号),“电子商务经营者申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的,允许其将网络经营场所作为经营场所进行登记。”因而这类个体工商户没有线下的“经营场所”,也即登记注册管辖的市场监管部门所在地,不能对应电商实际经营地是合法正常的。此外,该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的“住所”(包括常住地),不属于实际经营地概念,只是登记管辖确定的个人住所地而已,尽管“住所”也可能成为实际经营地,但需要证据证明。换句话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在无证据证明“住所”属于实际经营地状况下,不可以推定其“住所”为实际经营地,从而进行案件的移交或者移送。
第四,同一电商实际经营地可能会有多处。以商品交易为例,货源组织地(仓储地)、发货地、退货地、指令发出地(电脑终端设备所在地)都可能成为“实际经营地”。当然仓储地、发货地、退货地等也未必一定是电商的实际经营地,如发货地很可能不是电商的经营地,而是接受电商指令发货的另外经营者的生产地或者发货地。
按照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长期以来形成的理念,凡是与经营有关的行为地,都可能成为“实际经营地”,因而这是一个较为广泛而复杂的概念。如果总局对此不作界定,各地认定会产生分歧,甚至大相径庭的分歧。
三、电商互联网广告监管管辖
关于互联网(大众媒介)广告违法案件的管辖规定,市管总局2号令第十条几乎照抄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原工商总局令第28号)第八条和《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原工商总局令第87号)第十八条的内容。
互联网广告违法案件,包括广告主和广告经营者的违法行为,“由广告发布者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辖”为原则。但对广告主和广告经营者违法行为案件的管辖作了两个例外:一是发布者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辖有困难的,可以移交;二是广告主或者广告经营者所在地监管部门“先行发现违法线索或者收到投诉、举报的,也可以进行管辖”。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未提及对“广告代言人”违法广告行为如何管辖的问题,照抄的市管总局2号令自然也不会提及。其实既然互联网广告案件的管辖原则已确定,那么“广告代言人”的违法行为自然也应该“由广告发布者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辖”,这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市管总局2号令第十条第三款“对广告主自行发布违法互联网广告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由广告主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辖。”并非是第一款“由广告发布者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辖”的例外,而是这一原则的延伸或者特定情形。
此处的“广告主”是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发布者于一身的主体,也即自己设计、自己发布为自己的商品做广告的行为。当广告主为自己的商品做广告进行设计制作、发布,主体定位上仍然是“广告主”,而不是广告经营者或者发布者。但既然是自己发布,也属于“广告发布者”地位,故此类广告“由广告主所在地…部门管辖”仍未脱离“由广告发布者所在地…部门管辖”的范围。
关于“所在地”,按照原工商总局28号令的执行情况看,各地还是趋于一致的,即行为人工商注册地;没有注册的,则为行为人线下“经营地”。由此笔者认为,不论实际经营地在何方,广告主或者广告经营者注册地市场监管部门对该主体的违法广告行为具有管辖权,反而“实际经营地”监管部门不具有管辖权,这也是特别规定优于一般规定适用原则所确定的。
四、电商的协助调查和协助执行义务履行
非电商平台住所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除前述特定情形外,一般情况下不具有对电商平台违法行为的案件管辖权,也无权对其采取行政措施或者实施行政处罚。但这并不意味着电商平台可以对异地市场监管部门置之不理。
《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有关电子商务数据信息的,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提供。”《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监督检查部门调查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可以采取下列措施:“询问被调查的经营者、利害关系人及其他有关单位、个人,要求其说明有关情况或者提供与被调查行为有关的其他资料;”市管总局2号令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也规定“办案人员可以要求当事人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一定期限内提供证明材料或者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其他材料,并由材料提供人在有关材料上签名或者盖章。”
笔者认为,上述规定中的“其他有关单位、个人”并不限于市场监管部门地域管辖区内主体,也包括异地的主体。《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五条“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要求…”并未限定“有关主管部门”范围,也即不排除异地的“有关主管部门”,故市场监管部门只要为调查违法行为需要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比如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三条赋予的职权,要求异地电子商务经营者,包括平台经营者协助调查,提供“有关电子商务数据信息”,并不得拒绝或者拖延。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原食药总局令第36号)第二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查处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有严重违法行为的,应当通知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要求其立即停止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按照原食药总局令第27号《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违法行为由“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所在地或者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监管部门管辖,故作出“要求其立即停止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协助执行措施的,应包括负责查处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违法行为的异地市场监管部门。
笔者认为,依据上述法律和规章的规定,非电商平台住所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要求电商平台协助调查和协助执行。当然这种要求协助的行政行为,不对电商平台自身权利产生剥夺或者限制,不体现监管权力,而只是一种要求电商平台履行法律规定的责任义务行政行为。电商平台拒绝或者拖延的,异地市场监管部门鉴于对其无监管管辖权,因而无权对其实施行政制裁,包括采取相应强制性行政措施或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但是,电商平台拒绝或者拖延异地市场监管部门的协助调查或者协助执行要求,仍然会产生法律后果。电商平台的拒绝或者拖延行为一旦被固定成为“呈堂证供”,异地市场监管部门可以提请电商平台住所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对电商平台的拒绝或者拖延的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制裁。
电商平台住所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一旦接到异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提请,性质上属于市管总局2号令第十七条第一款所指的“其他部门移送…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按照行政处罚程序办理,并回复提请的异地市场监管部门。
五、电子商务监管的各地相互协作配合机制
自原工商总局49号令确定平台内经营者违法行为由平台经营者住所所在地监管部门管辖的监管体制以来,造成了各地协作配合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的撕裂。特别是“职业打假人”的兴起,导致网络交易投诉举报量突然变得异常巨大,一个职业打假人,可以一次性发出一百多件投诉举报信。这也使平台经营者住所所在地监管部门不堪重负,仅“移交”就需要花费很大人力和物力,深圳、广州、上海、北京和杭州等地都成为“移交”和“被移交”的重灾区。有的“被移交”的监管部门甚至义愤填膺,责问“移交”的监管部门,你们什么都不作,就知道“移”!有的甚至拒绝接收“移交”;也有的自设门槛,要求“移交”的监管部门必须满足一定的证据要求才予以接收。
笔者认为,修补或者完善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配合协作机制,仅凭市管总局2号令第四十二条等规定,还是远远不够的。笔者的想法是:
一是需要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电商平台,特别是大型、特大型平台往往是当地的“纳税大户”,别说当地县级局难以撼动电商平台,即便更高级别的监管部门也未必奈何的了。说白一点,某种“利益链”的存在,是情势所然,与腐败、不正当等无关。因而依靠弱小的当地监管部门去监管电商平台,从一开始已经注定其无所作为或者不能有大的作为。这就要求,市场监管总局要在制度上更进一步完善,有必要打破“独家”承担的局面,因为“独家”监管的本质是违背“双随机”原则的,必须切断“关系”链,保障公正执法。这就需要考虑“多家”监管,这有利于电商平台的规范化和合规性,一双眼睛盯着,变成多双眼睛盯着,自然要容易发现问题,也容易纠正错误,从而促进电商平台朝着合规、合法、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是开展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相关方的结对签约等活动,形成互利的协作关系。比如原先形成的“长三角地区”的江浙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作机制、十五城市工商机关协作论坛等,每年轮流坐庄,进行交流,增加了解和信任。
总之,案件管辖是否明确,各地之间如何配合协作,直接关系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监管电子商务的效率和作用。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以及消费者权益的行政保护效应产生,都离不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电子商务的监管效能,也即离不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电子商务监管职责履行。市场监管部门监管电子商务任重道远!
2019年1月3日于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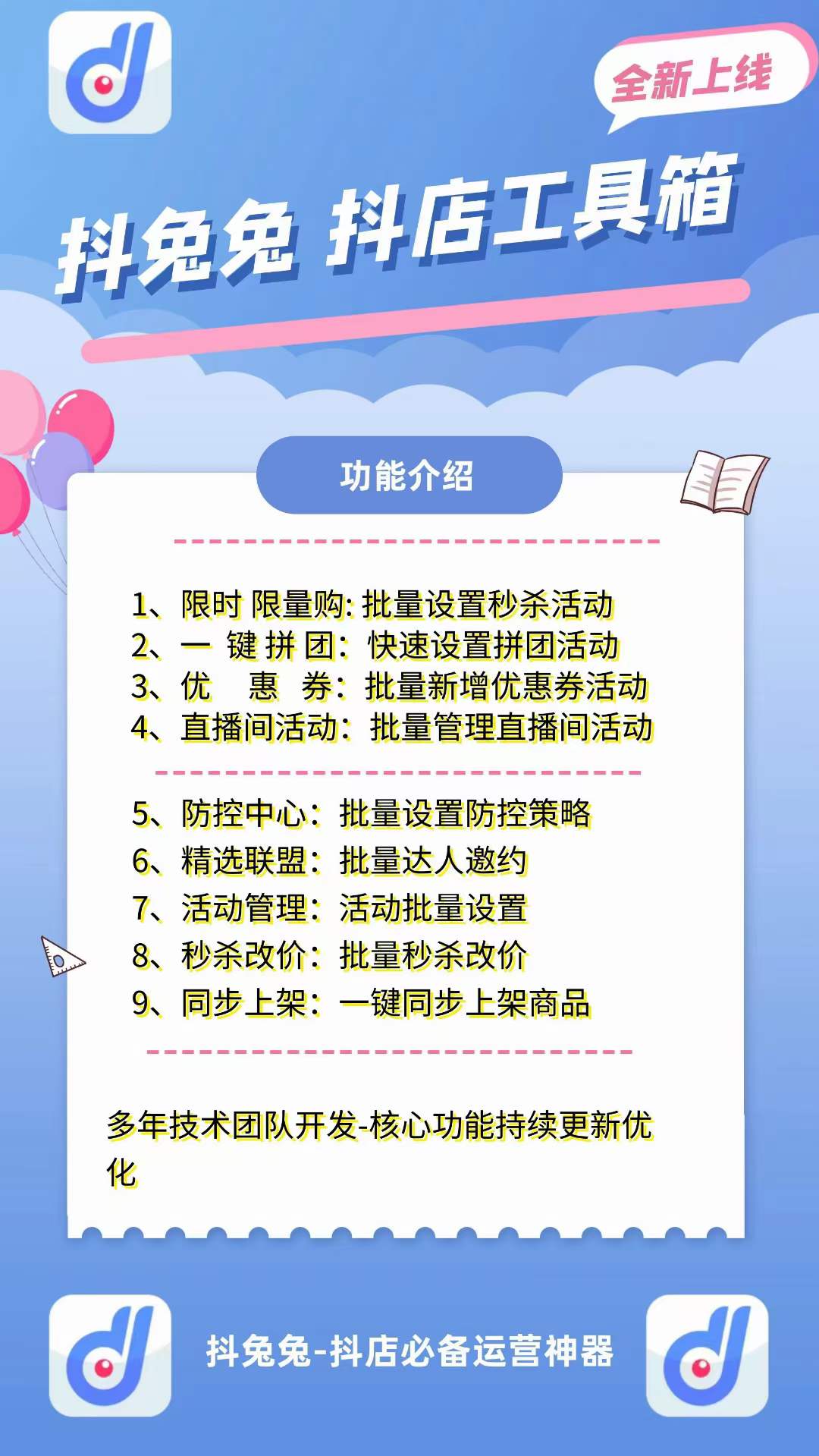











发表评论